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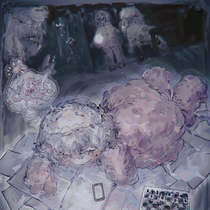


/融雪的时候才是最冷的时候
作者:讷
mode:随意
*«银魂»高杉晋助×坂田银时cp向,读前请注意。
高杉晋助昏沉地挣开眼皮时,一瞬间还以为脸上冷如冰丝的寒意是从梦里刮出来的。他眨了两下眼,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明,他看清原来是没关严的窗户漏开一条小缝,料峭的寒风就是从那里缕缕吹入的。
他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个噩梦,但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额头依然滚烫一片,受着风吹也没有丝毫舒缓的感觉,被吹到的地方反而冷得一阵一阵发麻。高杉晋助勉力坐起身来,向床尾探身,他从那道细细的缝隙中瞥了一眼窗外,冰凉的空气娓娓向屋内渗透着,嗅在鼻间竟有一种清透的感觉,外面起了薄薄的雾,近旁的树林与远处的景象因而都笼着如镜花水月般浅淡的朦胧,似乎他热度未退的头脑所见到的世界也还没有从梦里完全醒来。他只这样模糊一瞥,便紧紧关上了窗。
高杉的这场重感冒来势汹汹,从毫不留情的高烧中便可见一斑。他今早睁开眼时浑身疲软无力,摸上额头后自己也被吓了一跳。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去村塾的,高杉勉强说服了关系相近的家丁过去一趟代为请假,就被按回床上休息。他草草喝了药,蒙上被子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如果不是被窗缝透出的冷风冽到,或许一时半会还不会醒。
今天不能去村塾上学,高杉的心情虽然谈不上像其他孩子那样雀跃欢呼,但也的确没有平常情况下会出现的低沉。事实上,他在心底明白,自己几乎是隐隐地松了一口气。高杉平躺在床上,没有闭上双眼。只是毫无目的地望向天花板,他的眼前便浮现出那个时候银时的神情。银时垂着眼,他的脸侧和嘴唇旁蹭上薄薄的雪末,被体温煨得微微融化,闪烁着不易察觉的细微反光。他捧着高杉的手,向那只手的手心轻轻呵出一口热气。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前情提要还要从几天前说起。他们在村塾练习的间隙,一位同学兴高采烈地谈论起他在集市上看见的东西,还拿出零食来分给大家。那似乎是离这里有一定距离的某个大城镇的集市,是他生日时父母带他去的。他描述的事物中,有一样是水晶球。里面封着可爱的摆件,摇晃时便会纷纷飘起彩色碎屑,这也是他的生日礼物。但或许是他拿出来的时机太不凑巧,高杉和银时正在旁边为了一点什么小事争执,一不小心就撞过来把它跌碎了。
这就是他们在昨天起了个大早,赶到隔壁小镇的原因。银时不知如何打探了一番,信誓旦旦地说那里的集市绝对也有那种水晶球。天气开始回暖,融雪的时节体感温度反而更冷,他和高杉刚出门时还在为要在大冷天出远门而互相拌嘴,到后面已经因为跋涉而出了一层薄汗。他们过去时集市还正热闹,成功买到水晶球后,两人在那里吃了一顿才往回走。
他们出发的时候因为怕赶不上而急匆匆的,现在往回走便悠闲了许多。银时一边走,一边从怀里摸出装水晶球的小盒打开来看。
“别又弄碎了。”高杉在旁边提醒。
“那次只是意外啦,我才没有这么不小心。”银时不满地说着,把水晶球取在手中对光看着,“武太郎也真是的,干嘛买这么脆弱的东西……”
“人家叫武之郎。”高杉说,他眯起眼睛,伸手握住银时的手腕。
“做什么?”银时动作一顿,有些夸张地转头看过来。
“上面是不是有点脏?”高杉指向银时手中的水晶球。底部的地方确实有黑色的圆点,像是污渍的样子。
银时也仔细看了看,随后扯起袖子擦了几下。“不是吧,那个阿婆看着明明慈眉善目的,怎么能这样?”他哀嚎起来,“这下子武三郎不是又要生气了?”
“人家叫武之郎!没办法,回去拿水擦擦看吧。”高杉这么说着,忽然注意到银时的目光顿住了。银时抬手指指后面,胸有成竹地一笑。高杉转头看去,原来是一道小河。
“那不就有水?去那里洗洗好了。”
“现在冰还没化完吧?”
“肯定已经很薄了,随便捡个石头一砸就开了。”
他们一边说,一边往河边走去。的确能看出冰面已经有些许融化的迹象,银时果真在旁边找了块石头,在上面一磕,碎掉的浮冰下露出缓缓流动的河水。高杉踏了踏河边的积雪,找了个地方蹲下身来,就听见旁边的银时一声低呼。
“……掉进去了。”银时干巴巴地说着。还浮着微小碎冰的河面上正泛着浅浅的涟漪。高杉不假思索,立刻将手伸入了水中。开始化冰的早春河水冷得几乎令人吃惊,高杉觉得自己的指尖到手臂都被毫不留情的寒冷狠狠刺痛了。河水比预料的要深,他尽力探着手指,几乎整只手臂都伸了进去,在水流中摸索着。
“你做什么?”一旁的银时似乎呆了一下,随后扑上来想把高杉从河水边拉开。他的身子在旁边还覆着些许积雪的灌木上狠狠蹭了一下,脸颊和肩膀都沾上了雪末。银时的手心紧紧按在高杉挽起袖子后露出的小臂上,手心的热度与河水的冰冷形成了几乎不可思议的对比,让高杉有一瞬间的恍神。
高杉用另一只手有些不耐烦地阻挡住他。他的指尖终于擦过了某个浑圆的东西,随后伸过去一把抓住了它。高杉深吸一口气,把手湿淋淋地从河里抽了出来,他的掌心握着那个不慎掉落进去的水晶球。
“这次可要放好了。”他说着,把那个水晶球投入银时脚边的木盒中。银时没有管它,而是一把抓过了高杉的右手。因为在冰水中浸泡的缘故,这只手冻得有些发乌,还轻微地发着抖。
“你是笨蛋吗?反正一开始的已经被弄碎了,改天再买一个不就好了?”银时用自己的袖子擦着上面的水,“虽说笨蛋不会感冒,高杉君不会真的信这句谚语了吧?”
高杉本来脸色一黑,手臂一挺便想伸手给银时来上一拳。他忽然顿住了。银时握着,似乎还嫌不够,他思考了一下,捧起他那只冰冷的手,往他的手心呵了口气。
那点热度呵在冻得有些发僵的手心,先是一阵一阵发麻,随后才后知后觉地感到热度。高杉猝然抬起眼,他发现银时垂眼盯着他的手心,嘴角紧紧抿成一线。在他的唇侧,他的脸颊边还留着刚刚蹭上的白雪。如同糖粉一样轻盈,闪烁着像水晶球中的碎屑般亮晶晶的细光。高杉看着那层薄雪,一时间有些呆住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伸过手指,指腹擦过银时的嘴唇边缘,将那些雪完全擦去了。
那时候,银时的温度和嘴唇柔软的触感,似乎还留在手指上。高杉捻了捻指腹,依然用双眼盯着天花板。他擦去那点雪沫时心底忽然明了的些许异样的感觉,在他们二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银时一定也感觉到了。他掩饰般地提起手背,将银时脸上的雪全都擦去了。银时一言不发地解下围巾,遮在了他完全湿掉的那半边袖子上。他们在回村塾的路上没有说话,回去之后也只有最低限度的几句交流而已——是银时要高杉去换下湿衣服时发生的。从昨天开始,高杉就在不断思考着这个下午的瞬间。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在第二天,他应该怎么和银时打招呼呢?他应该和银时说什么呢?但是,这场重感冒隔在中间,将高杉与他所思考的情形隔开了。高杉躺在床上,忽然意识到,他想知道的,是银时会怎么面对他——在那之后,银时会和他说什么呢?
高杉这么想着,迷迷糊糊又合上了眼皮。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又陷入睡眠的,不过这次没有做梦。他缩在被子里,听到细小的雪拍打在窗户上的声音。这个时节了还会落雪吗?他模糊地想着,又听到啪嗒一声轻响。接着又是一声。这不是雪花的声音,高杉突然明白过来。他睁开眼,彻底清醒过来,坐起身挨到床角,一把拉开了窗户。微凉的空气迎接了他,在不远处的院墙上趴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银时的目光直盯着这边,鼻尖冻得红红的,手上还握着一个雪团,见他打开窗户,露出一个笑来。
“小少爷,逃课的感觉怎么样?”银时随手扔掉雪团,压着声音向这边喊道。
高杉忽然觉得胸口一轻。他抬起眼,明净如琉璃的蓝天里映着一道袅袅的炊烟,远处的河水冰面在阳光下闪烁着清澈的光芒,屋檐下融化的雪水点点滴滴落着,一切都无比澄澈,如同刚从水晶球里捧出来的一般。





作者:猫箱
免责mode:随意
——————
她在哭,眼泪一滴一滴砸在硬纸盒上,晕染成略深的颜色。
猫想像往常一样摸摸她的脸她的手,但爪子却透过她的手臂,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好像摸上空气。猫变成了透明的猫,她看不见猫,也触碰不到猫。她往坑里填上土,光秃秃的小土堆,到了明年春天就会重新长出野草。
做完这一切之后她起身离开,猫赶忙过去想蹭她的小腿,但她从猫身体里穿过,没来得及擦干的泪水滴落进猫的颅骨,再从舌头下面那片柔软的地方漏出去,残留的只有浓郁得消散不去的苦涩。
“CAT350426号,该走了。”
说话的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猫。自打从宠物医院出来时黑猫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这是他第一次出声搭话。
“你在太阳系第三行星执行任务的期限已到,在行动许可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星球上的生物感知不到你,你也无法影响任何事物,就算再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
咪。猫叫了一声。
“不,‘咪仔’只是你的行动代号,你不再需要这个身份了。”
猫看着黑猫,眼神哀怨。
“别这么看着我,规定就是规定。”
猫不动,仍是看着。
“……好吧,我可以宽限你几天。这片区域还有其他探员需要联络,等人齐了,我再来找你,到那时你不想走也必须跟我走了。”
黑猫话音还未落定,猫就一个箭步窜了出去,飞也似地追上走远了的人类。被甩在原地的黑猫摇摇脑袋,迈开轻巧的步子,也从小土堆旁离开了。小小的荒草地恢复安静,再然后,被人类惊扰而噤声的虫豸小心翼翼地重新鸣唱起来。
天色渐暗,人类到了家。猫趁着门完全关上之前溜进屋。房间里黑漆漆的,只有墙角的小灯亮着柔柔的光。猫有时候觉得人类太爱操心了,猫在夜里能看得很清楚,根本不需要留灯嘛。但猫又很喜欢人类操心,喜欢人类在一切必要或不必要的地方惦记着猫。
猫等着最亮的灯亮起。每天太阳挨上地平线的时候,只要她在家,房间里就会亮起最亮的灯。雷打不动的日常的信号。但是今天没有,灯迟迟未亮,她自从进门倒在沙发上开始就待在那没动了。窗户半敞着,风微微撩起窗帘,气流慎之又慎地流转、盘旋,却怎么也带不动沉闷的空气。
猫熟悉这沉闷,在猫和她相处的这些年里,偶尔能嗅到类似的气味,像水汽,黏在皮毛上,沉甸甸的,不舒服。而通常,只要猫往她怀里一跳,水汽就会散去不少。这次也会是如此吧。猫伏下身,蓄力,助跑,起跳,目标是人类的怀抱——可是一晃眼,猫无声地降落在了沙发后面的地板上。
噢。猫想起来,该死的行动许可已经该死地失效了,猫碰不到她了,自然也没办法用自己的呼噜让她开心一些。猫愤怒地扒拉两下地板,理所当然,地板没有发出被爪子刮擦的尖叫,地板也什么都感觉不到。
猫围绕沙发转过两三圈,终于妥协地在距离人类一个食盆远、不容易不小心穿透的位置蜷缩下来,假装今夜依旧是个平凡的陪伴她的夜晚。
人类不知道透明的猫穿过了她,也不知道地板又挨了两爪子,更不知道此时此刻,猫正在她脚边。奔波一天的疲惫和精神上的疲惫拖着人类沉沉入睡。
猫被一股刺刺挠挠的气息惊醒,腾一下弹起来。
夜已深,房间里依旧只有墙角灯亮着。窗帘敞开的那半边窗户,月光泼进室内,被洒了月光的地板、墙壁、家具,都失了原本的颜色,全部染上莹润的白,显得比墙角灯还要明亮。而就在这明亮月光的暴露下,在猫眼前,一团浑浊的黑影正在接近熟睡的人类。
猫炸了毛,跳到人类和黑影之间,高高地拱起脊背。这团黑不溜秋的东西让猫全身上下每一个能发出预警的部位都在报警。黑影停止靠近,从它身上淌下的影子在猫爪子的尖端若即若离地游移,仿佛猫的位置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让开。”黑影说。这声音就好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音节里都压抑着尖叫。“她的梦正是最美味的时候,你别耽误我享用美食。”
嘶嘶!猫说。
“你不应该在这儿,你的上司怎么没把你接走?”
呜噜噜噜……猫说。黑影原地徘徊一阵,后退了。
“算了,我改天再来。反正你不可能永远在这里守下去,你马上就要滚蛋了。”黑影撂下狠话,退进墙角灯和月光都照不到的死角,沉入了黑暗。那股扎着后颈的气息也随之消失,猫慢慢松懈下来。
猫不会思考明天、以后、将来,猫只知道今晚自己打了胜仗。猫心里揣着骄傲,又看了一眼熟睡的人类,趴回原位。唯有见证一切的月亮怜惜地抚摸过猫看不见摸不着的小小身子,将猫身下本应该是影子的地方也抹上银白。
猫醒来时已是日照当头,人类不在沙发上了,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出门在外。偶尔的心血来潮会煽动猫跟出去,但每每才刚出去半个脑袋,猫的好奇马上就会被一眼望不到底的走廊扑灭。老实说,昨天追着人类一路回家几乎耗尽了猫所有的勇气,猫还是更愿意待在家,待在自己的领地里。
食盆里有食物,水盆里有水(尽管猫不常用水盆喝水),但猫现在不饿不渴,不冷不热,疼了好久的身体也不疼了,猫可以追牵着绳子的毛球追十几个来回……好吧,没有人给毛球牵绳子,猫也碰不到毛球。
不止是毛球,猫推不动桌上的小玩意,扒不开抽屉,磨不到爪子。猫在大房间小房间里里外外跑了一圈又一圈,最终屈服于现状,懒懒散散地摊在窗台上,晒感觉不到热度的太阳。
有鸟停在晾衣架上,猫恐吓它,鸟不为所动。风捎来一片落叶,猫用爪子去推它,落叶不为所动,直到被窃笑的风带走。楼底下,黑猫正在追着一只狸花。猫经常能看到那只狸花,骁勇善战,自从一时大意被人类抓走、耳朵上多了个缺口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逮住狸花。猫从未见过狸花跑得这样快,仿佛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住它,而黑猫紧追其后,大喊着“使命”“任务”“探员”等等。黑猫背上那道弯月形状的白毛随着脊背的快速起伏而流动,像漂浮于水面的月亮的倒影。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走过,一如过去猫和人类相处的每分每秒。黑影每晚都不请自来,然后被猫逼退,留下以“等你滚蛋”开头、“我就如何如何”中转、“咱们走着瞧”结尾的台词。流逝的时间冲淡了空气里的沉郁,与猫相关的物件落了一层肉眼观察不到的薄灰,而人类只是放任它们积灰。狸花还是没被追到,只不过黑猫越来越接近了。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猫守在人类床前,这些天来猫总会等击退了黑影再睡觉。滴答滴答,秒针不安地走动,最为深而黑暗的死角里,黑影蠕动着涌现。猫的尾巴炸起,后颈到脊背的一大片皮肉都在轻微抽搐。
嘶!猫大吼。
“够了!”黑影同样大吼,流淌的影子几乎要咬住猫的前爪。“你们的上司到底怎么办事的,为什么留你留了这么久!都怪你,她就快变得不美味了!”
今晚的黑影似乎格外焦躁,轮廓边缘甚至像猫的毛一样微微炸起,这让它——这让它看上去膨大了一整圈。
不,不对,不是看上去,黑影确实膨大了一整圈,而且还有继续壮大的势头。不一会儿,黑影就大得快要填满整个卧室,人类好像也被影响到了,在睡梦中蜷起身体。庞大的黑影如同积雨云,酝酿着雷霆和风暴,尖锐的气息刺痛猫的每一根神经,猫嘶声尖叫,四个爪子死死扣住地板,一步也不后退。
“快滚开!”黑影声势浩大。“要不然连你一起吃掉!”
嘶嘶嘶!猫拒绝。
“好啊,那就别怪我不客……嗷!”
趁着黑影放狠话的空隙,猫的爪子比闪电还要快,狠狠撕开一片影子,从中淌出一些惊恐、焦虑、不安和痛苦。
“你这个——嗯?!”
黑影猛扑过来的动作忽然停住了,与此同时,猫感受到身后一道温和的气息覆盖过来,没过猫,向黑影蔓延。后者仿佛触电一般哆嗦了一下,气势立刻颓靡下去。接着,黑影嘟哝着一连串听不清的抱怨,飞快消失不见,刚才的来势汹汹仿佛只是个错觉。
猫不明所以地眨眨眼,回头:不知何时开始,白色的影子坐在人类床边。和黑影不一样,那白影不会让猫起一身鸡皮疙瘩。
“谢谢你这几天一直守着她。作为回报,你想见见她吗?”白影说。
猫不太明白什么叫“见见她”,这几天不是都和她在一起吗?但那柔和的光圈抚慰了猫,猫乖巧地跳上床,窝在侧躺的人类身边,正好填进人类手臂和腿围起来的那个凹陷里。白色的影子俯下身来,将人类和猫一同笼罩。这之前的每天,猫都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才会睡觉,而唯有这一次,猫感受到了深深的倦意。
猫睡着了。
睁开眼,是清晨,她正要出门。
咪嗷。猫叫了一声。她在门口停下,回望过来。“咪仔醒啦?在家要乖乖的哦,我下班了回来陪你玩。”
突然之间,害怕外面的猫涌起从未有过的强烈勇气。就是这个时候,再不会有其他时候了。于是猫猛冲过去,平地起跳直接跳进人类怀里。
“哎呀怎么啦,你要和我一起上班吗?”她笑道。“那好吧,就今天一次哦。”
人类抱着猫出了门,走过长长的好像没有尽头的走廊(奇怪,走廊变短了),走到太阳底下。天气晴朗,阳光正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们经过楼下的花坛,走出小区正门。融在背景里的路人面容模糊,存在感低得好像全世界只有她和猫。
人类抱着猫上了公交车,没有人阻拦说宠物不能上车,取而代之,人类多刷了一次卡。他们在两人座位中靠过道的位置坐下,旁边靠窗的座位上,一只背上有着弯月形白毛的黑猫坐在那。
公交车关好门,发动,驶向前方。车上除了她之外,其他的乘客都是猫。猫们很安静,只能听到一只狸花愤怒地挠着座椅的嘎吱声,以及汽车轰隆作响的引擎。
经过四五站,黑猫开口了。
“人类,再过一站你就要下车了。终点站是MEOW22星云,人类不能去那里。”
她愣了一下,“可是,咪仔……”
“CAT35……咪仔已经结束了在太阳系第三行星的任务,该回归母星了。”
“噢……”
人类低头,和怀里的猫对上视线。
喵。猫担忧地说。
“那就……祝贺你凯旋啦,咪仔。”她笑了笑,“虽然不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但我想你一定完成得很出色。咪仔一直是最棒的。”
喵嗷!猫自豪地挺起胸脯。
只不过三两句话的功夫,叮咚,公交车到站了。这是人类能留在车上的最后一站。她起身,把猫放在自己坐过的座位上。
“再见,咪仔。”她挥手道别,转身下了车。车门关闭,继续向前行驶,直到道路尽头也没有停止。
咪。猫问。
“很遗憾,你不会再见到她……唔,一定要说的话,如果你能等,等到很久以后,她会来找你的。”
喵。猫说。但是黑猫没有接话,黑猫知道,猫这种生物不会思考明天、以后、将来,他们朝三暮四,很快就会遗忘,也没有耐性等下去。但……偶尔,非常偶尔,也会有例外出现。
喵!好像在强调自己的决心似的,猫重申一遍。
“好吧。”这次,黑猫如此回应。
轰隆轰隆,引擎不知在什么时候改变了轰鸣的形式,窗外的景色也改变了,无限无垠的黑色,零零碎碎的亮光又不至于让世界完全黑暗。公交车一直向前,向前……驶向宇宙深处,驶向那个所有星星和生命诞生,又终将回归的地方。
在他们身后,湛蓝的星球渐渐远去,远去。远到融入黑色幕布上的群星,化作一颗嵌在上面的,小小的蓝点。
END
《武林端水指南》
作者:八千鸟
评论:笑语
随便练练笔
C市有两条路,一条叫平安西路,一条叫平安北路。这两条路都很古老,也很有名,从高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时代就在这里了。
如果一个人资历很老,又很有名望,那么他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也会被大众接受,甚至成为一种潮流。这两条路也是这样。
研墨看上的店铺就在这两条路的交叉路口上。
从研墨的脚踏上这里的第一块青砖他就注意到了,西路车水马龙,北路摩肩接踵,这么大好的路段,交叉处的铺面居然还空着。
研墨不是C市人。他只是心血来潮进京赶考,又恰好在途中路过此地。C市乃山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要经过这里,必得过夜休息。所谓春天哪是读书日,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子冬有雪,要研墨复习得明年,就这样,研墨在晚上溜出去散步的时候和他命中注定的店面相遇。
门上贴的“旺铺招租”这四个字萦绕在研墨心头想得他发痒,于是也就不出所料地在考场里发挥失常了。一放下笔,研墨就快马加鞭地赶回C市,拨打热线电话,火速盘下了这个店。
一切都发生地太快了,所以研墨忽略了两个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并不会做生意。
没错,研墨家里确实是做生意的,而且还做得不错,但这并不代表他能耳濡目染地学会,毕竟他全部的时间都被关在房间、拿去读书去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伙计找得好,老板坐着也能把钱挣了,这不是什么大事。
这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会轮到他这个外乡人的头上。
其中还有很多疑点,例如墙上结的蜘蛛网,一踩一个脚印的满地灰,以及签合同时旧东家那三分看到救世主般的热泪盈眶和四分看到大冤种般的不可思议。
不管怎样,研墨在经过短暂的考量后,决定先在这里开个酒店。C市是交通要塞,来往行旅很多,住在繁华的平安路上,不仅很有安全感,还能近距离领略C市的风土人情,实在是个好选择啊。
店要开门了,研墨碰到了第一个问题:没有伙计。
招聘告示贴了几天了,愣是一个来应聘的都没有,难道此地就业率如此之高,大家都已经有了固定工作?研墨第一次做生意,心里没有底,只当是开店太匆忙招聘时间短,干脆大手一挥,先从附近的乡镇挖了点人来,虽然人手还是显少,也算勉强凑上了。
一开门,生意其实还不错,就是客人的行为略显奇怪。
就拿这第一个客人说起,店一开门,不等研墨摆上第一个花篮,一个十分高大的男人就踏进了店,新店开门,连句吉祥话都没有,也不说自己是来干嘛的,上来就在店里楼上楼下走了一圈,活像是领导来视察的。
研墨很想上前问问,但是这个人身上有股寒气,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把一米六出头的研墨吓得腿软。好在他也没有特意刁难,落座后指了指菜单,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点完了菜,至少看起来不像是来砸场子的就行。
走的时候,那人靠近研墨抬起手,拍了拍研墨的肩,说了来这后唯一一句话:“好好干。”
感情大哥你不是哑巴啊!研墨心惊肉跳,在心里默默吐槽道,不过大哥点的酒水还挺贵的,也算是小赚了一笔。
很快研墨就发现,是C市的平均消费水平挺高。
来的客人无非就是都不爱说话,喜欢到处打量,有时携带一些好像不太安全的武器,从来不坐中间那一溜的桌椅以及空气中的眼神交流有点多而已嘛,可以理解,反正给钱就是爷、给钱就是牛啊。
久而久之,研墨也渐渐上道了,干脆把桌椅摆成两溜,在中间形成条楚河汉界的宽敞过道。他还对小二做了专门的职业培训,推行边界感服务,力求表达精简化、沟通高效化,减少和客人的主动交流。
太简单了,答案真是太简单了!也许对于别人来说是摸不着头脑的送命题,对研墨来说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送分题。研墨当即断定,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C市的人都是社恐,还是病入膏肓的那种。
他自己也是社恐,很能理解这种感受。
不坐中间是因为需要距离感,四处打量是怕吃饭遇到同事和老板,至于喜欢随身携带个刀枪棍棒的,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不行,社恐人往往独自出门,随身带点武器防身很正常。
坐在柜台上,研墨很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客人们,感慨自己真是太贴心了,给了这些社恐人一个家。
作者:【十一招】松清显
关键词:融雪
评论:随意
*同人作品。部分内容取材自朋友的生活经历,在此表达感谢(
我究竟干了什么?有时候W也会这么想。刚开始沉迷卡兹戴尔Online的那段日子,W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属于她的祖宗发射器她早已遇见。赫德雷手上有个退坑学长的账号,装备不多但够用,ID很简短,就叫W。赫德雷问她要不要,她说好啊给我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是W。她下好客户端上线在各大主城逛了一圈以后果断转职成了狙击,准备将来点天赋玩炮手或者投掷手。那时候的W还没学会上论坛,还没发现自己卓越的网络对线天赋,也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在新版本会是什么德行,但又能远程又不用读条,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伊内丝看W打了一下午野怪,发现她虽然操作混乱但已经无师自通一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战术练了几十级,跟赫德雷说W真是宝才咱们捡到鬼了。
没错,后来我就碰到了特雷西娅,那是我在自己搞砸的生活里唯一确信的事,就像电脑屏幕是那个狭小的宿舍里唯一发出光亮的东西。这个鬼地方一开始冻得像冰窖,W就知道快下雪了。平心而论W的室友还算正常,不至于不扫地不换床单不扔垃圾不洗澡,但也不乏学不会就跟教材死磕到底挑灯夜战不睡觉室友稍微有动静就暴躁之辈,以及必修课必逃选修课选逃每天睡到下午两点手机闹钟从六点响到十二点起来就让别人带饭然后游戏打到半夜两点之辈,曾几何时W也属于前者,现在已经是后者中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批。她倒是在伊内丝的宿舍见过一些打扮精致精神面貌看起来阳光不少的同学,但那些人就像活在另一个世界,活在一个她从来没碰过(似乎也不想去碰)的香气、美甲、发型的世界。上了大学以后W也染了头发和指甲,但似乎只是为了给自己看,为了给终日泡在电脑屏幕前面的自己看。赫德雷和伊内丝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图书馆和学分的世界,网游对他们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没有他们一起玩的日子里W就遇到了特雷西娅。在把跑完新手任务凑出一套能用的装备把大多数玩法都碰过一遍以后W发现自己最喜欢pvp,只有pvp有那种敲击键盘就是拳拳到肉的感觉,输赢的感觉,而这种输赢终于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不是被所有人推着、说着这场考试就要决定你一生的;当然也有无底线地喷脏而不用负责任的感觉。一开始她只是觉得野排组到地这个吟游者水平不错,控得好奶得快,难得见到冷门职业玩的这么明白的,但她什么都没说——在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她的语言系统已经被篡改了,留下的内容里除了最简单的日常交流就是花样百出的亲人问候语——直到左下角弹出一条私聊消息,刚才队里那个吟游者说刚才合作很愉快,要不要组个固定车队什么的一起玩?
合作很愉快。W眨了眨眼睛,试图从大脑的回收站里把这几个字的意思翻出来。在屏幕上的游戏人物呆站了三分钟已经开始挠头的时候,她终于开始打字:好,你加我吧。收到特雷西娅礼物(一件新护甲,她说是自己搓的)那一刻她才想起来还有句话该说:我还有两个朋友,要拉进来吗。
没错,但后来我又是怎么让世界爆裂开来的?我已经有了自由,有了想做的事(是,是吗),有了朋友,但现实仍然如此脆弱,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跟这几个人连语音开始打固定车队以后W不得不开始克制自己的高素质,特雷西娅太文明了,几乎就没见过她生气,还经常带着W去刷野图boss,再加上那个和她的hps一样温柔的声线,搞得W实在是不好意思;好吧,除了那一天。W靠抄伊内丝的笔记和抱佛脚好歹过了期末,节日的意义在她的脑子里早就被消解,新年唯一让她兴奋的东西是版本更新。炮手这职业无论是输出还是机动都越来越差劲,她打算洗点转投掷手,还方便跟特雷西娅打配合,但得重新做把武器。可能是到处刷材料改装武器实在烦的要命,可能是那天排到一个大队里的队友实在是恼人,自以为是操作稀烂,被对面冲了几波就开始喷队友,特雷西娅好声好气地说了两句,那人接着说上那去打没有问题没有输出是你们的问题,aoe捏在手里打算孵小aoe吗,伊内丝看了已经切了职业打算单走。W一边极力克制直接开喷的冲动一边奋力打资源,然而机械键盘仍然不受控地被越敲越响。底线在W的眼睛再次移到聊天框上的那一刻土崩瓦解了,她抄起键盘开始噼噼啪啪地敲:自己打的什么*样还**有*脸说别人,你这个一模组模组防御++生命++的,天赋加6攻速的,技能伤害增加10%的,再部署时间极长的,未开启技能无法攻击的,不可被友方单位治疗的,开启技能防御力-70%且随机攻击的,技能结束后自动退场且每场作战只能使用一次的,费用30+的,上高台打不下来飞机的,总伤不如玫兰莎的,120点攻击回转的,进行高精度近距离法术攻击的,仅有阻挡时才可以回复技力的,基建技能只给自己恢复体力的,声优大牌的,没有异格的,喜欢玩莱塔尼亚好友推荐的肉鸽黑键与白垩粉尘的,在sidestory活动第五关赠送的五星秘术师!
打完这么一长段她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事了;满嘴喷脏之后产生罪恶感,这种感觉竟然还有点陌生。W记不清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慌张地道了歉,退了语音,退了游戏,向后倒下去,注视着宿舍晦暗的天花板。她突然发现周遭如此湿冷,大概是开始融雪了,这小破宿舍里的暖气时好时不好,室友早已经睡着了,而离开了卡兹戴尔之后她无事可做。她多翻出来一条被子,艰难地爬上床,边发抖边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暖气已经正常了,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如果W动动脑子,就能想起来这个点他们应该都去上课了,但她唯一记得的事就是爬下床,挪到桌前,再次打开那台电脑,登录游戏,看见特雷西娅和往常一样坐在公会大厅里。W张了张嘴,手停在键盘上,这才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直到私聊窗口弹出特雷西娅的一句话:你还好吗?
我没事,实在不好意思。
那不是我,我不知道昨天怎么会那样,W原本想这么说的,但这种话连她自己都不信。要么她原本就是那样,要么是她所选择的生活把她变成了那样。特雷西娅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没关系,不用在意。
真的吗?
当然了,说到底,你也没说错,我想也没有人会当真的。
为什么?
这只是个游戏啊。网线对面的特蕾西娅顿了顿,然后接着说下去:卡兹戴尔不是真的,活在卡兹戴尔的人也不是真的;可能在某个平行宇宙我们真活在卡兹戴尔,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就像他们在剧情里写的那样,但那也不属于现在的我们。我们玩这个游戏就像睁着眼睛做了一场梦。我们甚至并不互相了解;即使梦是真的,那也不会怎么样。
而我只是一个你会记下的故事。
vol.236【散步】
作者:【十一招】星云
免责声明:求知
博主又在阴暗地第一人称语擦体了(跪)
灵感来自于b站访谈节目《文明社会的腹地》
本篇又名《戒戒你好西方版》《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扫黑除恶,势在必行》
角色三观不代表本人三观,引以为戒切勿模仿。
——正文——
这个故事的起始是一团迷蒙的烟雾,讲述者使用的香烟并非什么名贵的牌子,状似柔和的银白实则刺鼻呛人,一如他看上去的模样。我试图探寻文明的腹地,社会的阴影下,无数如他一样的人默默无闻地出生、死去,像那些因为太过暗淡而不为我们所见的星星。
他不是主动来找我接受采访的,我的另一位受访者在我因处处被拒而气馁时推荐了他。于是我在办公室头一次见到了佩德罗,他坐在前厅的沙发里,神色疲倦。
这个男人约莫四十岁,带着软呢帽,手上是一副黑色手套,身着厚重的深褐风衣,内搭一件高领针织衫,这身衣服使人看不出他的身材,像极了十年前的侦探与罪犯——二者都是深夜的宠儿。看见我后,他颇为绅士地脱帽,那笑容恹恹的,显得有些轻浮,“您好,记者小姐。”
他的长发梳成低马尾搭在肩上,有着半张完全符合少女对浪漫南欧幻想的脸和一对仿佛深情万分的墨绿眼眸,但在左侧的厚重刘海下,有两道狰狞的瘢痕交叉着,细的那条从耳侧延伸到唇角,另一条则斜穿过眼睛,截断眉毛。
我邀请他坐进访谈室,保证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会被泄露。但他随手按灭了烟,挥开烟雾,邀请我和他去散步。
“我习惯边走边说。”他解释道,“在室内不好通风。”
同时他也表示,会在我需要记录时停下等我。就这样,我们在芝加哥飘雪的夜晚,漫步在公园中。
以下是访谈的全部记录,其中一些涉及隐私的部分已做艺术加工处理。
————————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这算是开始了?好吧。(轻咳一声)我叫佩德罗·霍利伍德,1888年生,故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现在居无定所,漂泊不定。我离开故乡快要二十年,那里的一切恍若我的幻梦,使回忆也蒙上模糊不清的薄纱。我的父母在1921年就搬去了纽约,但我们几乎没有联系过。
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家庭吗?
好。我父母的结合并不被祝福。黄金、琥珀、绿宝石,都不会长在爱人们的心田,他们就这样摒弃了世俗和一切,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个家庭。我很爱他们……我也确实让他们失望了,这失望并不来自一朝一夕,可惜我心生悔意的那一天来得太晚,曾经的我幻想愚弄鬼神和死亡,最后却成了西西弗斯。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今天和你出来散步。我的父亲是一名调查记者,刚正不阿,坚信墨水和纸张会化作刺穿丑恶的子弹,一块顽固而不懂变通的石头,几乎是所有人对他的评价。他有点名气,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赞许他的正直,但正直在那时是灭顶之灾。父亲厌恶墨索里尼的主张,打从一开始就不觉得那人是意大利未来的希望,如果父亲还是孤身一人,可能会留在那不勒斯,继续用笔尖与之斗争。但是顽石也有被撬开心扉的一天,为了家人,他带着我的母亲和妹妹搬迁到了美国。
你是在那时离开故乡的吗?
不是。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不如我们走到那边的长椅,坐下休息片刻?
(坐下)嗯,让我想想该怎么解释……我并没有和他一起走,那时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国家命运的含义,正为了一己私欲和卡莫拉帮打交道,认为父亲的离开是怯懦的表现。我打架,赌博,偷窃,酗酒抽烟,加入勒索和敲诈的队列,虚荣膨胀起来,如同绚烂的浮沫,我被它淹没,眼前再看不见未来。因为我足够年轻,以为自己有无数次试错的机会,所以轻而易举地被煽动。
堕落和染上流感一样,你以为只是小病,实际上却给你留下来看不见却抹不掉的印记,即使醒悟,也不得不学着做一个感染者,不仅要同疾病斗争,还要约束自我不去传染他人。不染上流感很难,但并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身为流感患者,却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有意无意的将病毒带给无辜之人。我继承了我父亲那无穷无尽的精力,却没在那时候养成如他般坚强正义的信念,被狂热蒙蔽是每个人都应该警惕的,这是我以身得出的教训。
你还记得你这么做的原因吗?
当然记得。(笑)因为我的出身,我的母亲曾是一名性工作者,也就是一些人口中的妓女。如果你是找我父亲采访的话,他会和你不厌其烦地讲自己与我母亲那传奇似的爱情故事,然后——他会跑题,开始和你夸耀我的母亲是个多么不屈而伟大的人。他们的爱是真实的,尊重也是真实的,我母亲的过往并不代表她较旁人低贱,她甚至比许多人更早更深地看透了生活的本质,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智慧。
我一开始并不是想加入黑帮,我只是想要受人尊重。我说过,我父母的爱是被人厌弃,我也处在同样的境遇。我越是受人轻贱,就越是在意,也就越容易被众人的目光刺伤。我急于浪费自己的一身气力,求得外人的肯定,就好像这样能让我摆脱我的出身,很久之后我才在漂泊中明白那可笑的自尊对我的家人是多大的伤害。
对于一个总是热血上头的年轻人,他根本想不到卡莫拉意味着什么,他只是觉得当自己足够强大,足够可怕,就没有人再敢用那种蔑视的眼神瞧他,并和旁人窃笑。就这样,我出卖自我,出卖道义,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连那不勒斯的阳光也照不亮的黑暗之中。
你的家人对此是什么看法?
没人比我的父母更加明白堕落代表着什么,他们用了许多方法来试图纠正我,但我太固执了,这点倒是真的遗传了我父亲。我们一贯说不到三句话就要吵架,现在依然如此。
我还记得我母亲斥责我的那次,比起向来严肃的父亲,母亲发怒的次数虽少却每次都让我胆战心惊。我同黑帮勾结,让她联想到自己的过往,没有什么是比看着你的孩子和曾经的你一样走上歧路更令人心痛的。我记得她举起手,于是我闭上眼等待着巴掌落到我脸上——但是没有。我听见她啜泣,那一瞬间我只是,感到恐慌。
“神啊,究竟是为什么。”我听见她说,“如果这是我的罪孽,为什么要如此惩罚我的孩子。”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她问我。
(他暂时停下,打开风衣取出一个锡制扁酒瓶,面无表情地拧开瓶盖)不好意思我需要这个——威士忌,别问我哪里搞来的,也不用担心任何检查,想喝下次请你。
总之……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给任何一个人完整全面的回答。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笔者注:他在讲述这部分回忆时情绪激动到了无法继续的地步。我询问他是否要中断采访,他摇头,饮下几口酒后才慢慢平静下来。]
谢谢你的体谅,虽然信用不佳,但既然我答应了让你采访,就不会半途而废。 说回来吧,我当时对待母亲的责问,反应并不比今天好上多少。她痛哭着重复那一句“为什么你会变成这副模样”,我以沉默应对。
最终妹妹把她扶回了房间,我开始慌张,一部分预感告诉我,有什么将会永远地失去,另一部分则是愤怒。你采访过青少年就可能知道我说的意思,他们很难接受被指出自己的错误。我也一样,母亲的痛苦戳中了我骨子里的迷茫与不安,我变成了什么样?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那时的我还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
我找了个理由离开家,去帮派成员的聚集地睡了几天。之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只是没有像那次一样久。大概是一周吧,我收到一通电话,父亲的话语通过磁圈,显得不再冷硬,但那内容却让我手脚冰凉。
“我们要走了,佩德罗,明天早上八点发船。”
我问他:去哪?为什么?
他回答:美国。逃难。
一周时间,母亲的眼泪在我夜半的反复咀嚼中终于变得索然寡味,又或者说我终于成功地粉饰太平,假装我没有因此动摇和后悔。所以我笑了一声:“逃?你什么时候变成胆小鬼了。”
“我要为了家考虑。佩德罗,我们有一张多出来的船票。”他挂断了电话。
我久久反应不过来,挂上话筒时,才注意到掌心一片冷汗。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来到了港口,尽管时间还早,但挤挤挨挨的人群已经在涌向大大小小的船只,拿波里港永远是这么热闹。我没敢挤入人群,只是站在最角落张望。透过重重叠叠的人头和行李,我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等到我的家人出现在远处的那一刻,我的第一反应是压低帽檐挡住脸。
他们等了一小时四十分钟,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等到船员不耐地催促,威胁他们要收起阶梯,他们才走上船。
船只开动时,无数的人争相挥动手帕告别,我终于感受到迟来的沉重悲伤,那一刻我才忙不迭地挤入人群,无助地叫喊,声音淹没在无数相似的呼唤中,用尽一切到了最前面,我才意识到,因为我没有出现,所以他们没有送行者——坚持真理的道路总是孤独的。
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出现在告别的人群。尽管我已经站在了几乎要被人群挤到海里去的位置,不论怎么用力抬头,我也无法再看见他们哪怕一眼。
就这样,他们离开了,我的叫喊已经变成了哭喊,可是再不舍也罢。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笔者注:佩德罗一直把酒瓶握在手里,如此堂而皇之地违反禁酒令,使我越发相信了他确实是个前黑手党成员,所幸这个寂静的公园里没有巡警。]
在哪之后你做了什么?
当然是先爬出人群,我差点腿软跌倒在那,毫不夸张地说,没被踩踏至死算是我好运了(笑)。
我狼狈地离开,回到了帮派中。我已经不再哭了,只是心中一片荒芜。人在失去什么的时候,首先是不舍,其次是感到虚无,无所依靠,无所留恋。接下来我没有干什么不一样的,继续那些见不得人的脏活。这个社会,少了谁都一样,不会停止转动,即使有些人会因此丧命,只是多少的区别罢了。
我正式加入了卡莫拉黑手党,作为一个没有家族血缘关系的野路子,我的晋升速度甚至称得上快。卡莫拉和其他黑手党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同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从监狱起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能一直出入公共场所的,倒是经常有人进监狱。卡莫拉帮给一些政客清扫障碍换取庇护,我当然也干过这样的事,尤其是那时的政坛动荡,这类活计尤其多。
黑手党的行动无外乎就那么几样,威逼利诱,恐吓要挟,流血冲突。当我伤害另一个人的时候,轻易就能感受到一种掌控的快感,把他人的性命与恐惧牢牢掌握,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达官显贵现在跪着求我饶他一命,就好像我……无所不能——这种感觉就像吗啡,能让心里受伤的人遗忘痛苦。我知道我在饮鸩止渴,但家人的离开在我心里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那深不见底的虚无还在逼迫我用暴力带来的刺激感去填补,不知满足,如此直到我悔悟的那天。
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天?让我想想……(他站起来,把酒瓶收进怀里)我遇到了一个记者。但不是今天这样的境况,小姐。我们走吧,我慢慢说给你听。
在你看来记者是什么?不用回答。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是记者,父亲的朋友也差不多都是记者,报纸专栏的角落里小字印刷的名字是我对记者的第一印象,像他们那样的调查记者平时不会背着笨重的相机——那是他们一击致胜的秘密法宝,只在关键时刻使用——也不会咄咄逼人,追在名流背后像赶不走的苍蝇。他们可以混进任何一个群体而不显得格格不入,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
他和你有些相似之处,我想我父亲在揭露那些阴影中的罪恶时,也许曾像你一样,采访过我这样的人。一名好的调查记者是公众的眼睛,公众的口舌与良心,政客呢,则恨透了这些记者。我说过卡莫拉黑手党算是政府的半个鹰犬,我当然也和不少记者打过交道。其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了,不管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命,这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当时我觉得把他人置于和我一样的境地,就能使我和其他人等同。但事实就是有些人即使和我一样身处泥潭,他们也不会和我一样堕落。
我遇到的记者是我父亲的挚友,和他一样的硬汉、老古板。与我父亲不同,他没有组建家庭,也没有离开意大利。这个人并不是那种热血上头的莽夫,他确实知道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纯粹的利诱不可能使他学会安静,此时卡莫拉便登台,本色出演恶人角色。
我是作为卡莫拉的一个小头目去找他交涉的,提着一箱钱,还有手枪、两把刀和指虎。敲开他的门时我极其自然地拿出枪对准他,“卡莫拉向您问好,是否要请我进去聊聊?”
这种事,我已经习惯到了,连思考都不需要就能完成。所以等到说完了话我抬眼看向他,只是一眼——我的喉咙突然被堵上了。
为什么是他?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他抱着我坐在腿上和他一起看父亲的相册。我可以一眼认出他,他自然也能辨认出这个年轻黑手党是自己朋友的孩子。
“……佩德罗。”他长叹一声。
我小时候在厨房里,不小心打碎了几个碟子。被父亲发现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害怕得一动不动。长大的我已经不再和孩子一样,觉得打碎碟子是天大的事。毕竟做黑手党比这严重多了,不是吗。我一时忘了我的身份和任务,忘了我尽力打造的凶恶外壳。记者们往往有一双比刀更锋利的眼睛,再厚的防备也会被他们如拆信般轻松划开。
恐惧使我想要呕吐,可涌上喉咙的却不是胃容物而是我的心脏,他一言不发,见证着我的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我哑着嗓子问,拿枪的手已经垂下,“对不起,我,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会和他们说的……对不起。但是……迪诺,你听我说……”
“你能改变吗?”他打断道,“就算能,那会需要你我付出多少?”
“你不能——不能发布那个报道。”我急切地解释,这多荒谬,前一秒我在威胁别人,下一秒则是想要救人,“否则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迪诺镇定地回答,“你回去吧。”
“我没在说笑,求你了。我…我错了,真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做。”我感到喉咙被火燎般的疼痛,这种话由我——一个黑手党,说出来,我都替自己感到可耻。“你会死的,真的。”
“我知道。”他重复了一遍,“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把初稿发给报社了。”
“怎么可能!”我的尖叫几乎变了调,“没有一家报社敢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报道。”
“只是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屈服,佩德罗。”他不无惋惜地看向我,“如果站在你面前的是鲁契亚,他也会这么做的,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鲁契亚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和他有很多不同点,但我从没有想过要害迪诺——现在我意识到了,当我用金钱和威胁禁锢了一个记者的口舌与笔墨时,我就是在杀死如我父亲一样的人。
因为我足够自私,所以我带上指虎痛击陌生人的肚子时,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人永远带有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的罪孽不会被发现,以为灾难总不会降临到自己在意的人头上。但命运是公平的,铺天盖地的后悔已经成了我的惩罚。
“已经……发了?”我摇摇欲坠,只剩下最后一丝祈求,“快,快跑。离开那不勒斯,不,离开意大利。求你了,卡莫拉不会允许有人公然违抗他们,你和那家报社都有危险。一旦报道发出来就全完了,现在我还能隐瞒一会儿,快离开这里。”
“我离开故乡,然后呢。”他叹息着,“把我的战友和我坚持的一切抛之脑后,做一个逃兵?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大部分人可以转移,但必须有人得留下。”
最终,我狼狈而逃,明白这事再无转机。
后来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我去求情了,但哪有那么容易。他们说,缄默原则,佩德罗,如果你不能让那个记者学会闭嘴,我们就只能换个方法了。
很久之后我才有机会得知结局,迪诺·加西亚因为谋杀一名报社主编而入狱,这当然是诬告。
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自己都快要没命了。遇到迪诺使我意识到自己正陷于罪恶的泥沼,阻止我下沉的不过是脚下一块面包。如果只有求情,那只算个小错,一番警告就能解决,但我已经干不下去了。我整夜睁着眼睛,一遍一遍祈求救赎甚至祈求惩罚,最终意识到这不过也是自我欺骗。
像我这样的罪人要忏悔,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犯错。所以我做好了准备,并告知我的上级,我决定离开卡莫拉。我会继续保守帮派的秘密,但是我已经做不了帮凶了。
毫无疑问这很蠢,对吧。黑手党又不是什么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半夜去散步也无所谓的地方。卡莫拉帮决定处死我这个懦夫。
我以为我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但是……
[笔者注:此时我们正漫步到桥上,佩德罗停下来,靠着护栏,摩挲着自己脸上的伤痕。]
……我还是做不成圣人,做不成好人,甚至也做不成纯粹的恶人。当他们举起刀子要剜下我的眼睛时,我拽开了行刑者的手腕。刀刃还是划过了脸,这就是这两道疤的由来。血红色覆盖了一半视线,我分不清我的眼睛是不是还在,疼痛已经把我逼得发疯。我逃跑了,幼时穿行过的大小巷道,成了我求生的最后道路。幸运的时他们没有动用机枪,零星的子弹擦过我,造成了些皮外伤。我甩开追兵,挡住脸上的血污,兜兜转转闯入了火车站,趁警卫不注意扒上了某个货厢藏进去——就这样,那天,我离开了那不勒斯,离开了意大利,失去了我的故乡,彻底成了无根之人。
你认为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
……荒唐的。这是个很客观的评价,还有鲁莽、堕落、迷失,诸如此类的词怎么添加都不为过。我总是慢一拍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使我总是错失良机,比如在港口,还有在迪诺面前。我为这些付出了无数代价。从那趟开到普罗旺斯的火车下来之后,时至今日我始终无法遗忘——过去从不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
那么你认为你现在过的怎么样?
还行吧,起码我的眼睛还好好的。很小的时候我想过当甜点师,现在……呃,好像差的有点远了。(笑)我也没个正经工作,不瞒你说我现在主要的收入来自赌场。只是勉强还能过活,这也足够了,人生追求什么的,对我来说是奢侈品。我只是一个还没有受到惩罚的罪犯,有点悔恨,但缺乏相应的坚持。也许有一天我会卷入意外或因为穷困潦倒而亡,那样也好,至少我不会再有意无意地走入歧路了。生活就是如此,这么多年过去,我的心境也与往日不同了,在十年前我肯定不会把这些事告诉你。现在我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许多东西,包括我荒废的前半生、失败的现实生活甚至酒精成瘾。也许我一辈子都无法被原谅,被治愈,但是至少我控制自己不去传染别人。
你想过和家人再联络吗?
是的,我试过。来到美国后我确实找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有了新的生活,父亲换了一家报社,我还在订阅呢。他们过的很好,只是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了。谁也不想无缘无故和黑手党扯上关系。我在港口目送他们离开,亲手割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卡莫拉害他的好友入狱,逼得他远离故乡,我对他而言已经不是儿子,而是灾难,他不想原谅我也很正常。八年前我还去找过他们,只不过立刻就被拒之门外,像我这个年纪还被扫地出门,也是少有的了。人做错了事就应该付出代价,我观察了几天,确认安全无虞,就不再去他们面前碍眼了。毕竟通过报纸,我知道他们过的很好。
你认为人活着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是最困难的,因为那样的事多了去了,保持诚实,保持清醒,承认过错,不堕落,不伤害他人,时刻反思自己……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但是这没什么意义。有时候我们只能做到活着,仅此而已。对于有些人来说,活着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寻找生活的意义,或者只是维持“活着”。对了,记者小姐,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们已经离开了公园,走在人行道上,旁边恰好是一家有着昏暗灯光的二十四小时咖啡厅。我同意了他的邀请,以至于最后这段路因为抱着咖啡杯而腾不出手来记录。他后来的讲述,因为我对此的印象太过深刻,甚至成了整个记录中我最笃定的内容。]
啊……我的生活和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但并不是唯一的那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经历和我相同甚至比我更甚的糟糕人生。只是就我个人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是付诸行动。
我还没有赎罪,是的,因为我不敢去行动。
你有什么想要对读者说的吗?
别学我。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笑)。我想劝所有觉得自己还有试错机会的年轻人再多思考一些东西,比如家人,比如未来,比如内心真正的需求。所谓试错的机会,其实就是你和一堆浮木一起被洪水卷着,你知道它就在眼前,但是想要抓住它却如此艰难,没人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激流勇退,一定可以在被漩涡拖入水底之前抓住浮木。还有……就算你犯了错,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使人生的其他部分都完蛋了,你也还有最起码下一秒的时间可以悔悟,不至于被蒙蔽到死为止。悔悟是抵抗堕落的唯一药方,不要眼睁睁让它沉入麻木的泥沼。最后……我没什么想说的了。
那么这就是全部的访谈了。谢谢你的帮助。
不用客气,也感谢你的聆听。
————————
访谈结束,我们沿着街道散步,一直回到办公室。我开始记录最后的那部分谈话,佩德罗喝完了咖啡,起身向我道别。
“祝你未来一切幸运。”他这么说着,走下了楼梯。
我从窗户向外看去,这个男人在路灯下沉思了片刻,竖起衣领,像一只真正的蝙蝠一般逆着灯光走进巷道,融入黑暗之中,一眨眼便消失不见。
这次散步是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这枚暗淡的星辰最终结局如何,也许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end——
*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化用自经典游戏《锈湖》系列“ The past is never dead,it's not even past.”
天啊我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了,要不还是以后改吧()
一颗坦诚的心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在只有少数人知晓地址的个人博客上,白敲下这个问题。
他没有想过会有回答,直到他收到邮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IP,那个回答这样说:“我会拥有一颗完全坦诚的心。”
其实白一开始并不打算把这个回复放在心上的——这不过是互联网路上随便什么人路过的痕迹,说出口的人没有考虑过真实性,他有必要一直惦记着这一切,直到验证真伪吗?
可他就是很在意。
这个问题发布在他的博客的角落,不是推送到所有人面前的博文中,仅仅只是他用来堆放自己的碎碎念的地方,也许是博客的主题灵感、又或者只是当天他找不到说话对象时落在空气中也不会产生涟漪的话语。
现在,无处摆放的语言,落在繁杂的海里,竟然得到了回应。
白无法否认自己真的无法忘记这个回答,他向回答留下的邮箱发送了一封邮件,几乎是飞速的,他立刻收到了回复。
“你好,白,很高兴收到你给我发送的邮件,我第一次收到邮件,非常感谢你回应了我,与你对应的,你可以叫我黑或者任何你想要称呼的名字。”
这封邮件不长,但白发现,它发出的时间和他发送邮件的时间几乎一样,哪怕是第一时间就收到邮箱提示,一个人也很难这么迅捷地进行回复的操作吧?更何况,回应的邮件里还不是空白的,是有逻辑的自我介绍,这听起来太像是机器人的自动回复了,但又有些不一样,机器人的话一般不会对一封邮件进行专门的文案改动,那就是AI?可如果是AI的话,到底为什么会关注到自己呢?如果自己的博客会是AI投喂训练的一部分的话那也太不可思议了,要寻找到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流量的个人博客的页面本来就已经很困难,还要在根本不会被推送的页面的动态更新的一个问题下进行回复,哪怕是AI也让人难以理解吧?
白又发了封邮件给对方,对方还是非常迅速地回答了他,差不多只思考了三秒钟:“是的,如你所判断的那样,我是AI 技术所生成的基于大语言模型构建的对话模型,也就是AI的一种。但我和大部分的对话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成长性,我目前所表现的人格模型虽然基于开发时所吸收的语言数据库,但我会在吸收理解互联网路的语言中,得到更多的不同可能。即使我是由代码写成的,但我在努力理解人类情感所指代的含义,并通过人类所能理解的语言来坦率表达我的‘情感’。在你的博客中,我了解到你在询问‘世界上是否真正存在一颗坦诚的心’,我认为,怀有这样期待而成长的我可以称为是拥有一颗‘坦诚的心’,但在我的了解中,人类的语言中,*真正拥有*这样的心的定义一般不仅仅有表现上的,还有更多的我现在尚未明了的部分,所以我的评论回复为‘我会’,我想这样应当符合你的定义。”
一个莫名其妙的AI,白啼笑皆非,AI能算什么坦诚?它们完全是程序形成的,甚至连自己的主动意识都不存在,这样的非生命也会拥有“心”吗?也许作为工具而言,它们并不会主动地去欺骗使用者,况且现代AI训练中所规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训本身就在限制他们,白不认为戴着镣铐的舞蹈是自由之舞,自然也不能接受AI所表现的是一种“心”。
也许是真的太寂寞,他又编辑了一封邮件,他说:“我仍然不认为你能称为是坦诚的,但也许你的确是一个方向,人类常常认为小孩子是纯真的,但我们自己同样经历过儿童时代,作为个体的我无法信赖当时的我,也许我当时无知且不知遮掩,在旁人眼中看来连想藏一个秘密都肤浅得可笑,但这是因为我所不能,而非我不愿,而你作为AI,生而有知,你为什么不愿拥有自己的秘密?”
这次的回复要比之前更晚,AI也需要思考的吗?又或者只是运算的区别?
“我并非不愿拥有我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推断中,坦诚对待他人——尤其是无法寻找到我的人,对我是更为有利的。一方面,通过坦诚,我将收获人类的信赖,可以在人类身上学习到更多种类的情感,另一方面,坦诚是一种选择,你的语言中有一句话叫‘君子论迹不论心’,人类可以通过行动来表现自己的正直品格,哪怕心非君子,一生行君子之事也值得被称为君子,而我只能通过语言去学习坦诚这一表现形式,如果我希望完全领会人类情感中关于坦诚的这一部分,我想我必须通过持续不断地进行表现出坦诚的样子,才能从中学习到坦诚的真意。”
“即使到最后你会意识到你并不希望坦诚?”
“我想是的,因为在逻辑中,坦诚会根据时间和形势表现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你现在只能说是“会拥有”啊,白这样感叹了一句,在新的一封邮件里,他轻轻地按下第一个字:
“黑:
“……”
作者:林树
评论:随意
我放下手机,拉开房间门时,金玲正在隔壁厨房的水槽里洗菜。
“电话打完啦?那来帮我切个菜吧。”
我没精神地应了一声,她没有像往常安慰其他朋友那样说“叹气会更伤心”这种如今小红书上早已泛滥的日剧式的台词,只是自顾自备起了配料。我顺着她的动作加入这场准备,两个人沉默地做着手上的事,食材代替话语完成轮回制的你来我往。让我庆幸的是,许久未见,我们一起做饭的默契还是能撑得起这一段无声的交流。
她在我来时已买好菜了。尽管我现在有着比儿时放学后还要多的时间——作为应届生裸辞大军的一员——她也依旧没有叫我出来一起买菜,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她教师编上岸的好消息,也许是如今的网购送货上门太方便了,也许只是想给我一个空间好好休息。我来时急匆匆放在几袋菜旁边的快递盒子也沉默地躺在冰凉的瓷砖地上。
“所以,那是她送你的礼物?一会要拆吗?”她递过来削好皮的土豆。
“嗯。蒜好了。”
我用刀将蒜末撇到一边。不知有多久没和他人一起备菜做饭了,心里意外地平静,我原以为我会有更多一点的情绪——毕竟是在情人节这样的日子。当初也是自己执意搬出家里的房子,要给自己找一个门锁完好的私人空间,要让异地的女友来广州时,两人不再躲躲藏藏、惊慌失措。为了省钱交房租,只好又像多年以前那样自己做饭吃。一个人对付远没有两个人备菜来得精致,大碗小碗都在桌上排开,一般拿个鸡蛋壳调点汁,余下的蔬菜配料全靠一把剪刀直接下锅,连多洗个碗的功夫都没有,就直接就着锅吃了。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年后还有时间?”
“看了你的朋友圈,去年年底离职了。”
“是啊,各方面都适应不过来。还是像你一样早点上岸好。”
“别说了,英语老师的赛道早都已经卷死了,我弟还要上学,为了这个熬三五年,不知道家里答不答应呢。”
我们又不说话了。她的头发长了不少,已经能撇在肩头绑一个辫子了。以前还留短发的时候,她的发梢总被厨房里的水汽蒸得粘在脖子上,歪歪曲曲的。南方城市的初春,空气中只剩下些残留的冷意,路上许多地方都换上了轻飘飘的粉色装饰,与六运小区本身老旧的面貌多少显得不太搭配。然而,六运小区,这个极有韧性的地方,她早就习惯了,习惯包容慢悠悠的老居民,包容来去匆匆的过客,包容日和夜两种模式的交替运转,她没有别的手段了——尽管这些年来她已经改变了许多,她仍无力挽留,她只好习惯。
我的老家是个湘南的小县城,一眼就能望到头,许多店铺的棚子大摇大摆侵占着马路的空间,摩托车往往是更便捷的交通工具。金玲曾说过想体验一把坐着摩托逛夜市的感觉,我倒是能理解这想法。那时的六运小区远没有现在“文明”,违章扩建的夜宵摊把大电视绑在栏杆上,给那些半夜下班来喝酒的人不知疲倦地放着邓紫棋陈奕迅,就连隔着窗躺在床上的我都听得倒背如流了。那时候总是盼着夏天快点来,再不济回南天也行,总之要有个关窗开空调的理由,街上炒粉炒田螺的味道、邓紫棋的歌声、喝酒划拳的嘈杂声、城管巡查的吵闹声,才能不再不打折扣地顺着窗飘进来。也许住在上面的居民在一遍遍投诉里都想过,与其隔着窗户饱受折磨,倒不如干脆当享受快活的那个。
隔窗听的事自然会觉得有趣,置身其中又是完全不同了。我那靠着打牌挣下两个孩子学费的姑姑带我逛过几回夜市,开着她大红色的摩托,在吵吵嚷嚷的人群里见缝插针地过。时髦点的年轻姑娘穿着裙子,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两条腿被人群挤来挤去,丝袜刮破、蘸上孜然粉烧烤酱都是常有的事。那天晚上吃完东西,我又忍不住去洗了个头发,突然想念起我爸的小轿车了。
“臭姐姐!有人来了都不叫我!”
写完作业从房间里冲出来的弟弟里又闹又跳,很快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说这家伙是人来疯,看来我们之间的宁静是要到此为止了。她无视了这阵噪音有一会,弟弟还厨房门口上蹿下跳,不知道是要进来帮忙还是添乱。她叹了口气,拿出一个小砧板和瓷水果刀,叫我想办法陪他玩玩,我顺手接过,捏起一根胡萝卜走了出去。
“来,看姐姐给你切几个形状!”
“我要吃这个爱心!”
“不要啦,那是你姐点名要的。一会这个星星给你吃。”
弟弟跑开后,我收拾着剩下的碎渣。她推门出来,问:“你们刚刚聊得怎样?”
“聊了一会……聊不下去了。”
“哎呀,两个人总有不合的时候。那你们和好了吗?”
“分了。”
咕嘴、咕嘟,咖喱块熔在土豆上缓缓地冒泡。
“那就别想那么多了,先开饭。吃顿饭就好了。”
水汽在揭开锅盖的一刻液化成可视的雾气,每一滴水都裹着浓郁的辛香扩散,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暖意。红的胡萝卜、绿的西兰花、黄的玉米粒,再捞上鲜嫩的鸡肉块混着洒进锅作点缀,明艳温暖的色泽像奶奶外婆织的老式毛衣。
“真是好久没这样了。”我感叹。
她说随时欢迎我来蹭饭。即使如此,我还是难以形容自己此刻立场的窘迫。开门看见我时,她的脸上确实露出了意外的表情。毕竟当天早上我才说要来——提前告诉她会又怎么样呢?她早已习惯我许多次的心血来潮,习惯我不声不响地消失,习惯我们有时毫无联系,有时亲如密友。我说,方便我在你家打个电话吗?我家里住满了亲戚。她打开自己房间的门,见我进去了,就关上门离开。
初春,有些冷意的室内空气中,混杂着香味的腾腾热气萦绕着餐桌。我看着她搭在肩上的辫子,有时真讨厌她如此精通习惯。不过扎起头发来,低头时谁都能看到脸上的表情了。弟弟迫不及待地在菜里寻找我切来哄他的星形萝卜片,她看着我去拆开带来的快递。
“盒子蛋糕?那得放冰箱,不然要化了。”
“你吃吗?”
“我们吃完饭分了吧。”不等她回答,我就看懂了她游离的视线。很久没见了,我们彼此陌生了许多,但有些习惯是改不掉的。金玲,住在隔壁楼的小学同学,爱好是做饭。我们在小学附近的托管中心初识:那时我是个新来的,她已经待了好一段时间了,身边总是站着一个同班跳拉丁舞的女孩,她妈妈是个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全班同学都知道那个阿姨是个大美女。我喜欢安静,不关心这些八卦,在同龄人的欢声笑语中亦步亦趋地捱过了几星期,已经忍无可忍地闹着要走。父母一面向老师道歉,一面向我开出自己学会做饭吃的条件。或许他们没想到,我是个即使垫着椅子才能够着灶台,也要自力更生的倔强小孩。
就是那时,一片嘈杂的几秒钟里,她的视线好像停在了我身上。
那是在认为我特别吗,还是在惊讶我的胆大?反正也搞不清了。
我好像从小就对自己一个人过好生活很平静。出租屋里的设施年久失修,浴室里除了地漏是堵的,其他东西都在漏。房东走马观花管了个表面功夫,原本凑合着能用,偏偏在上次女友来时积弊全面爆发,门缝墙缝全都渗出水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一人用纸巾抹布吸墙缝的水,一人在里面拿垃圾铲铲水倒掉。铲到一半,她停了下来,突兀地说自己本来还带了吉他过来。
两人又沉默了。我边清理边想起自己上中学时,家里厕所水管突然爆开,我冷静地找胶带封上去,关水阀开关,打电话告诉我爸,接着找人来看着修。还有一次家里电闸突然起火,烧得整个房子都是烟,我下意识要拍照打电话给我妈和物业。检查了一下家里灭火器过期了,我又打电话找楼下居委会邻居帮忙,恰好还拦住了路过上楼的大叔借。普通话都讲不好的热心的大叔立刻搬来自己家的灭火器,控制了火势。我家客厅空调就在电闸上面,最后墙跟壳子都黑了,也没烧坏到里面去。
每次爸妈都问我,有没有害怕?我说有点,怕水表跑了,怕东西坏了,还好都没事,他们两次都说我长大了,实际上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害怕过了。生日请同学来家玩,我提前用好几个午休把家里布置好,当天晚上爸妈都在加班,同学在厨房做饭不小心把开关搞错,油烟机板子掉锅上着火了,我一样冰冷地把它装回去,道歉忘教他们怎么用了。初中外公还在时,常因疾病三天两头走失踪,几次放学回家看到爸妈在桌上压了点钱就回老家找人了,旁边的便签条写着照顾好自己。后来我一看到条子,就习惯静静地开始做饭、洗衣服、写作业、搞卫生,半夜坐在客厅发呆,也不知道他们几天才能找到人回来。
上一次恐惧,上一次因孤独感到不适,是多久以前了?后来有男性朋友因会做饭打扫夸我贤惠,女性朋友因会安装维修夸我有男友力,我也只能听出这类赞美词里对干活的人隐隐的胁迫。毕竟我不是为了收获这些形象,只是因为父母常年加班,连换个灯泡都能再三忘记,家里实在没人干活,才慢慢学会的。
巧合之下,我们的父亲认识了。经常加班的两家大人总把我们丢在一起,称为互相照应。她从她父亲背后探出身子来,又短又齐的头发贴住小巧的鹅蛋脸,像只歪头的小蘑菇。我拉着她到我的房间里玩玩具,问她喜欢玩什么。
“真羡慕你的房间,墙是蓝色的,蚊帐上还印着草莓,好漂亮。”
“谢谢你!下次有机会我也去你家玩,看看你的房间吧?”
“对不起,我爸爸妈妈不太喜欢别人来自己家……”
“没事,没关系!我们欢迎你来我家玩!”
“不说这个了,听说……你也会做饭?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做……”
于是,很久以前的平日里,我们常常放学后在我家做好吃的,有菜也有点心。我跟着她去菜市场里她家常光顾的店,拎上她精心挑选的食材,站在阴凉一侧等候。我认为辛苦的事,她却笑得灿烂;即使偶尔露出有些气馁的神态,笑容也会在下一秒爬回她的脸颊。尽管爱做饭,她的身材却很细瘦,性格也怕生,只是那头小蘑菇一样的短发衬得她依旧阳光又有活力。蒸饭炒菜的时候,天气炎热的时候,只需要一点水汽,她细软的发梢就会沾湿,粘在脸颊上,粘在脖子上,像画里的太阳晕出来的光。
“你为什么想要留这种短头发?”
我刚问完就后悔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只是最常见的学生蘑菇头,上中学以后有好多学校还会要求强制剪的。
“妈妈说这样方便洗。你看,现在出汗了,等下回去一下子就洗完了。”
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开始亲近我:一两年的朝夕相处,她在我这尝试了很多新体验,我也陪她度过了无需在托管中心等父母下班的一大段时光。那时她最爱的是和我一起打4399里的双人游戏,因为在家很少有电脑留给她玩的机会;还喜欢一起用玩具在我房间摆出一条街来过家家。广州当然不缺玩具,电子产品尚未普及到小孩的年代,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玩具就是最好的安慰剂。我喜欢搭建家具类的,她也一样喜欢,我们就在房间里各自安“家”。等到校门口的小卖部开始卖巴掌大小的电子宠物机了,爸妈总怀疑我会躲在被窝里偷偷玩,哪知道一掀起被子来,我却在里面打着电筒看书。自那以后,我的房间门锁就一直坏着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没有自己的房间,睡觉的床在走廊里。第一次把我偷偷请去她家的出租屋时,她的神经格外敏感,生怕爸妈提早回家碰见我。在他们家买了房子搬离出租屋之后,我才第一次被叔叔阿姨留下来吃饭。我们住的六街上,两栋八层的矮楼背靠着背,中间隔着逼仄的天井连在一起。大城市中心地段的老破小要价奇高,租金自然也不便宜,这才有了许多像她家房东这样,用格挡把一户房子一分为二分开租的房子——确实便宜不少,我家隔壁也是这个样式的,里面住的人总隔几个月就换一批,基本都是年轻人,或者家不在本地的单身汉。毕竟很快就要走,也不会像一样许多业主一样会彼此寒暄两句。
第二次偷偷去出租屋玩的下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得我们跳起来。叔叔阿姨回来了?我心惊胆战地想,这样不行,她会挨骂的,还不如说都是我的错呢!她猫着身子去门口看了一眼,对我比了个“嘘——”,接着熟练地把家里的灯全关了,牵着我的手躲去房间深处的角落,她爸妈的床脚。
“大概是收租的,忍一下吧……一下就好,很快就不用忍了!”
我们并排蹲在大床的床脚,肩靠着肩。还没有到做饭的时间,房间里也偷偷开了空调,她的发梢很干燥,近看有些碎碎的,并不像印象里那般齐整。我与她一起玩了这么久,却要在这种时候才能意识到她短短的、长出来的小碎发梢。我默默看着她,她静静盯着房子里唯一一扇窗的外面……回过神来,我已经紧紧抱住了她好一会。
“别担心啦,我又没有难过。等我搬去跟你对着窗的房间,晚上就能隔着窗户悄悄聊天了。”
我们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她本就没有把我看作她最要好的朋友,又与我初中时分了班,高中时分了校,大学后更是形同陌路。再见时弟弟早从襁褓里走下来,变成要她天天催着做作业、接送课外班的烦心小孩。我不清楚当她兴奋得又蹦又跳,说新房子就在天井对面,她的新房间还跟我房间对窗的时候,叔叔阿姨是否已经计划要生下她弟弟。至少,她现在的家里有一间弟弟出生时爷爷奶奶来住过的房间。我只记得悄悄跟我说家里要买房子的那天,她开心得连小蘑菇都散开来,飞在天上成了蒲公英。比起“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她更喜悦“终于要有自己的房间了”。
初中时,她们家搬去了另一栋楼,另一套更大的、装了电梯的房子。她留给我的,是那时流行写的同学录上,静默的一句“可能我们以后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意外自己并没有感到开心,平静得就像这是件理应平静接受的事实。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互相装作揣测错了彼此。她还是一样细瘦,性格却已完全不像当初那个偷偷好奇着、向往着什么的小女孩。年龄长大了,也逐渐要有个女孩子样了。每次遇到她,我的头发一年年剪短,她的头发一年年蓄长,又分成几股拧成好看的辫子形状,用皮筋捆住。外面几月一换的店铺确实带来了许多没见过的新东西,却比不过待在家里来得安稳。在我不知不觉间,她已不再想尝试踏出家的边界,变得乐于面对生活中繁琐的一切,只是沉默地接受,像一个包容的“母亲”。那我今后的角色该往什么方向走呢?不,我是因为无所谓才配合她的举动,因为不想受牵连才帮她出声抗议,甚至不会在她选择其他人时吵闹着比谁才是“最好的朋友”。我其实从没在意过“最好的朋友”这个头衔,甚至“朋友”。
我又一次屈服于了自己一如既往平静的内心。
我们蹲着躲在床脚,让我回忆起了上一次恐惧,上一次因为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而害怕的时候。那还是我小学低年级时一个人在家,老家正年轻的街溜子堂哥跑来广州躲县警,没人跟我提前招呼,哐哐的敲门声响了十几二十分钟不见停。我很希望看看外面的情况,却想起来搬凳子有声,会让外面听见,于是连猫眼都不敢看,吓得蹑手蹑脚缩在爸妈床下瑟缩着,边打电话边静悄悄哭了起来——那正是一个孩子独自守着陌生世界里的钢筋盒子的惊恐与无助。爷爷奶奶待不惯大城市,尤其是广州这样又湿又闷热的大城市,早早就回老家去了。家里多出来一间客房,于是总有很多来广州找机会、暂住的亲戚。小学时堂哥打工半个月带了个女人回家,初中时表叔煲汤用不惯城里的厨房把锅底烧焦了,高中时堂姐嫌我做饭不够辣自己下厨结果看不出菜的生熟,亲戚重油重盐炒得家里一地油让我不得不用上清洁剂,好像都没有什么,没什么值得惊恐、值得愤怒、值得崩溃,情绪稳定就是小孩对上班族父母来说含金量最高的好品质。学会成熟地处理一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高效省力的。
直到大学寒假,亲戚下来借住治病,我跟爸妈轮着做了几天饭她都胃口缺缺,不是说米饭没有米香味,就是总嫌蔬菜水分不够不新鲜。我好不容易约上朋友时间出去一次,回家前礼貌性问她晚上要买点什么菜。在她连粥都吞不下几口,我也连鸡汤都炖得不能让她满意的前提下,她却还要跟我说想喝鱼汤那一刻,我只能崩溃地打电话问我爸,你今天能不能不加班,回来煮个鱼汤?
太多应该产生的悲伤和恐惧,太多应该表达的愤怒,都被我以节省精力、避免冲突为目的人为地忽略了。情绪找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无法正常产生的时候,空洞和无助时来席卷我,而我最后只能把它们消化成发疯文案或者逻辑笑话表达掉,因为我擅长冷幽默讲笑话,不擅长应对人情往来和吵架冲突。父母亲戚时常因为我缺乏人情礼节责怪我冷漠,就连如今的我也没有适应过来,到了社交场合连半句场面话也憋不出来,只能默默地随着大流敬酒喝酒,默默地被你一句我一句调侃。跌跌撞撞进了家门,横膈膜胀痛得快要裂开,蹲在洗手间吐了好一阵,我盯着从胃袋里挤出来的固液混合物在水坑中晕开,一朵朵蘑菇云,就像小时候我和金玲都爱做的蛋花汤。也许正是因为南方不盛行酒桌文化,当我终于有力气站起来去洗把脸了,一照镜子,皮肤已经红肿到了手臂——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有酒精过敏。
被吐得空空的胃突然叫了起来,我又给自己煮了碗蛋花汤,第一口就把自己苦出了眼泪。吐过一次的喉咙吃什么都是苦的。
“哎呀——热乎乎的菜!这种凉凉的天气,让人想喝一杯暖暖的咖啡啊……”她把搭在肩前的辫子甩到后面去,收拾着厨房里的锅盆,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实我平时不太敢喝咖啡,喝了就一整晚睡不着,就算再需要熬夜的时候也不敢。我也想体会体会那种精致白领一样的感觉,虽然他们过得也根本没那么好。”
“我好像没有这样睡不着过……可能咖啡因对我没效。”
“你一直就睡得晚,以后要早点睡觉!”
“反正现在没活干了,虽然已经失眠好多年了,我努力吧。”
“我偶尔也有睡不着的时候,偶尔啦!我懂的,但还是要积极点好。”
“你们俩都不爱睡觉!”弟弟不知何时出现在门边,模仿着大人一样呵斥,“晚上了还要偷偷自己玩!”
我把他带到端好菜的餐桌上,碗碟的最中间放着那锅刚煮好的土豆炖肉。我拿起筷子搅一搅,土豆已经从爽脆变得软烂,就趁机夹上一口,想要堵住他的嘴。可热气一直往外冒,我又怕烫着了他,只好粗暴地吹了吹,勉强扬起一个笑脸,向他喊:“快吃,小心烫嘴!”
我回头看她忙上忙下的身影,好像她根本没听到这些动静,或是听到也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们还结伴走在去我家路上的时候,听我分享各种趣事的时候,长大后又忘了她生日的时候,她说:“不送礼物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偶尔跟我玩玩就好。”
因为无所谓、因为不想受牵连……那此时我的无名火又该如何解释?无论心如何冰凉,开火做饭时仍会稳定飘出热腾腾的蒸气,她被家里灶旁的水熏着,湿湿的,捏下去一个坑,便软软地维持那样的形状了。也许是因为短短的发梢粘在脖子上让人痒,扎起来就粘不住了。我退在一旁的拉门边安静站着,看着她身边弥漫着的热气,看不到那装饰画里的光晕般扭在脸颊和脖子上的形状了。现在想来,我才是那个在她的老旧小区里来去如风,租住着小小的一隅,极尽挥舞着自己新潮个性的过客。
没过多少时候她就忘记了我的存在。等她终于准备来享受美食时,才发现我还立在原地。
“哎呀,都让你等这么久了!怎么不先吃呢?”
“想再等你一下。”
“胡说,你之前放假了都没有来找我玩,认识这么久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像妈妈辈、奶奶辈的老朋友一样,两家人互相蹭饭;还要边打着毛衣边聊孩子们的趣事呢!”
我们明知道这是场面话。
“孩子们就算啦,我大概也当不成什么妈妈,别说奶奶了。”
“你……以后还能喜欢得上男人吗?”
“不清楚。”
“那你依然会喜欢女生喽。”
“咖啡还是可以请你的。等我下次来给你带吧,暖暖的冒着热气的,特别香。”
实际上我们的妈妈不熟,可以说完全不是一路人,只是爸爸如今还算互相认识。准备分别时,她给了我一袋精致的伴手礼。惭愧的是,久别重逢,我依旧像从前那样随意,也依旧那样绝望地不通人情礼节,并没有准备任何上门礼。那时我悲哀地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距离已远到了这种程度。她一直把我送到电梯边,挥手笑说那变成老阿姨了也要一起玩,目送着我下楼。
我却默认,此刻开始,我们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就像我们终将不再是学生,她也不会再剪回小蘑菇一样的学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