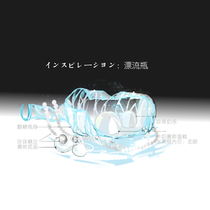





作者:轻拍拍
评论:随意
杨泊下班回到小区,看见七岁的儿子杨云辉正蹲在沙坑里挖沙子,更小的女儿坐在幼儿车里吃手指。男人站在原地,向楼上张望了一下,厨房亮着灯。
“妈妈呢?”杨泊在幼儿车旁边站定,检查了女儿的奶瓶和尿不湿。
“在厨房做饭,她说她明天要回姥姥家。”杨云辉趴在沙地上,聚精会神地审视自己花了半个小时挖掘出的水渠走势。“上楼吧,饭差不多做好了。”杨泊看了一眼手表,打算把儿子从沙坑里拉起来。
他穿着皮鞋踩进沙坑。干燥的沙砾细腻又光滑,让走惯了木地板和地毯的杨泊一时不太习惯。接着他又走了两步,最后踩在儿子从地下深处翻出的饱含水分的深褐色沙土上,这里的触感像水泥路一样稳重、安定,却柔和。
“好吧。”儿子意犹未尽地爬起来,拍了拍膝盖。杨泊把他牵出沙坑,一边拍掉儿子裤子和衣服上的沙子,一边回忆刚才踏在沙土上的触感,仿佛一头牛在反刍。
自己过去一定无比熟悉这种感觉。杨泊生于农村,在田野里度过了不知多少时光,而现在沙土令他感到陌生。一种极其荒凉空虚又难以名状的感情无声地侵袭了他。
女儿突然的哭声令杨泊不得不放弃了这缕思绪。他推着幼儿车,带着儿子走进电梯。晚饭间,妻子宣布了自己必须回一趟娘家的事实,周末只能由杨泊一人照看两个孩子。
“杨云辉,你现在已经二年级了,当哥哥的要照看好妹妹。”妻子离家前对儿子说。然后又对杨泊说:“要是实在照看不过来,就带着去你妈那儿。”杨泊答应了。
妻子离开后十分钟,杨泊已经喝了两罐啤酒。杨云辉从卧室冲出来,一把抱住他的腿:“爸爸,今天我们去哪里玩?”
“哪里也不去,”杨泊说,“你可以去楼下挖沙子,记得带上你的妹妹,你要照顾好她。”妹妹此时躺在杨泊和妻子的大床上,刚刚入睡。她安静的时候像个天使。“不过要晚一点,你的妹妹刚刚睡着。”
儿子撅起嘴巴:“不要,我昨天挖的水道一定已经被别人弄坏了,我不想再挖一遍。”他跑回房间,关上了门。凭良心讲,杨泊绝对一百个愿意把孩子们送到自己父母那里帮忙照看,可他又不愿意这样做,至少不愿不曾努力过:他隐约觉得这是一种投降认输。
最终,在女儿哭了今天的第三次时,杨泊想到了一种折中的方法。他拿起车钥匙:“杨云辉,记不记得奶奶家北边有座山?我们去爬山吧。”
这实在是个一举多得的主意,既排解了儿子过剩的精力,又能让老人帮忙照看女儿,还不至于落给妻子偷懒的口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连杨泊本人都只有模糊的感知:昨天沙地的触感勾起了一些往日回忆,他想去重温那段时光。在他进城读高中之前,老家的后山是他最美好的休憩地,是他童年的缩影。
“每年春天,山上都会开满金黄的油菜花,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杨泊穿上一双崭新的运动鞋,这双鞋只在单位组织长跑时穿过一次,随后便束之高阁,他花了不少时间才翻出来。一路上,杨泊都在讲述他小时候如何在后山飞岩走壁、采花摘果。儿子眨巴着眼睛,对不久后的冒险表现得很兴奋,不断问着“蜜蜂不会蜇人吗?”“山上有小河吗?”之类的问题。令杨泊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在回答儿子时没有感到丝毫的不耐烦。女儿在后座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或许她也希望父亲和哥哥能有一场愉快放松的旅行,很配合地一路保持情绪稳定。
一小时后,他们抵达了杨泊的老家。儿子站在车旁,向北方的小山坡张望。它充其量只能算一座矮山,大概有一百米高,孤零零的,四周没一个兄弟姐妹。杨泊没望见什么金黄的油菜花,山上一块绿一块褐,像旧衣服上乱七八糟的补丁。
等他们进了屋,杨泊的母亲不断端来水果和零食,父亲又泡了一壶新茶。老家的房子有一种冷清的气氛,令人难以久坐。儿子不住地看杨泊,希望由他提出爬山的安排。杨泊喝到第三杯茶,又踌躇了一会儿才开口:“杨云辉想去爬后山,我带他去玩一会儿,妹妹就留在家里——”
“哎呀爬什么后山,这都快五点了,该做晚饭了。再说外边天多冷啊,这才刚到二月,你们都多久没回来了……” 杨泊的母亲指的是农历二月。
男孩立刻闷闷不乐起来。杨泊还没开口,杨泊的父亲先开口了:“男孩子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是该多运动运动,再说现在天长了,六点也不会黑天。”杨泊微笑起来。
“你开车累了吧,在家好好休息,我替你带孙子玩一会儿。”杨泊的父亲领着男孩出了门。杨泊张了张嘴,慢吞吞地把茶水喝光。
“这老头,就是自己想出去玩。”杨泊的母亲揭完短,又招呼杨泊:“帮我把芹菜择了,晚上炒芹菜。”
芹菜几乎有杨泊手腕那么粗,根部没多少泥,杨泊猜母亲买菜时把泥甩掉了,这样可以少称半两。后山上可没人种芹菜,至少杨泊没见过。他见过不少野葡萄一类的浆果,孩子们什么都敢往嘴里塞。
杨泊手上的动作越来越慢,几乎停止,但在随后的某一秒,他择菜的动作突然变得干净利落,像瞌睡的人猛然惊醒。他把择好的芹菜放在案板上,走进卧室,此刻母亲正抱着妹妹,用奶瓶喂奶。
“我出去接他们。”杨泊说,伸手去拿床头的手电筒。
这只手电筒有大红色的塑料外壳,纹路笔直。杨泊推开开关,手电的光并不显眼,天还没黑。他又把开关关掉,左右手递来递去。通往后山的路平整又宽阔,杨泊记得过去经常有大卡车拖着黑烟,满载泥土和石子经过,但现在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他走出二里地,道路开始上坡,熟悉的感觉回到他的体内:这条路他走过千百遍,右手边应该是一片高粱地。天色比先前暗了几分,杨泊打开手电,发现右边是连绵的围墙,围墙前面是刚刚移栽过来的稻草人般的低矮树干。
杨泊愕然地看着眼前陌生的光景,说不清是失落还是害怕,他不太想继续前进了。杨泊走进围墙前的绿化带,扶着树干,在干硬的泥土上踩了几脚,触感与水泥道路没什么不同。
“爸爸,你怎么来了!”道路前方传来儿子的呼喊。男孩一路冲下坡,喘着气停在杨泊身边。父亲的身影远远地落在后面。
杨泊从绿化带走出来:“来接你们。山上好玩吗?”他把手电的光打向道路另一侧,那里什么也没有。
“也就那样,哪有油菜花,爷爷说早就没人种了。”儿子埋怨地说。
杨泊露出尴尬的笑,毕竟一路上他都在讲述后山的油菜花。天色更暗了,路灯还没有点亮,儿子没看到他的表情。
“不过比小区里的沙坑好玩,”儿子补充道:“明天上午我还想来。”
杨泊的手指触电般曲了一下,过去的自己隐约与眼前的孩子重叠了。他猜想,或许在过去的自己眼里,后山其实并没有那么有意思。 即便如此,他还是想再看一眼。毕竟过去的自己已经一去不返了。
“明天我带你来。”杨泊说。儿子欢呼起来。杨泊也欢呼起来。







多么美好的一天啊,鸟儿在歌唱,花儿在绽放,像这样美好的一天,比亚尔...“啊——真是够了!”...捡到了一个濒死的人,正在救人。
虽然学校有教急救知识,动手方面比亚尔也有学过但...他现在很后悔自己当初走神没有在意教导主任录播的急救类型判断,他根本无从知晓该用什么手段施救。在他身边的精灵球一直在摇晃,但除了本人无法使用...本人?“抱歉了!”比亚尔握着男人的手抓住精灵球,丢出,那摇动终于冲开了精灵球,放出其中的一只差不多娃娃来,火急火燎地查看男人的情况,然后着急的向比亚尔挥手比划着什么,让他在紧急照着指示帮助后又额外花了两秒才意识到,这位明显成年且不知道大了自己多少的男人,“是被饿晕的?!”
仅仅是摄入水分并不能立刻让一个被饥饿感放倒的成年人,可这种状态的肠胃必然是没法以固态摄入营养的,比亚尔只能选择粥水作为紧急摄入营养的手段,那边由差不多娃娃用能量饮料间歇喂入补充糖分,这边先迅速将米淘干净,多龙端锅烧水,米淘换三轮后水中加油盐短暂泡着,将之前就解冻要使用的肉临时切成肉碎入滚水,多龙以汤勺挑去浮沫,撒盐,但为了速成此时不能以缓和的方式,比亚尔当机立断把此时浸了肉沫的水倒进高压锅,再把米一并丢进去,高压加热,并在起锅后迅速盛出一碗来火急火燎地送到病人身边,由差不多娃娃仔细吹拂致安全温度,再轻柔送进似乎开始对外界起了本能反应,主动配合摄入饮食的病人。
“...到底是怎么做到把自己饿晕的,明明那么大一个人了。”妈妈一样的差不多娃娃道谢过后将男人扶到一侧铺好的睡袋上休息,秉持着送佛到西的思想,比亚尔想了想,决定帮他把一些粥水用一个保温杯填满,又找了个登山用的带子将一个短披带的水壶加长,装上能量饮料,一并先放在他的身边,看着食材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先拿树果给他做一份果泥来填补维生素的空缺——他是真的没料到在路地上可以见到败血症的前期症状。脆口的酸甜味树果去皮切割小块,以破壁机打碎,再用研锤仔细碾压细碎,手法虽因时间短促而略显粗暴,但吸收的效率大抵不会差太多?就这么想着,比亚尔端着果泥转身...“...人呢?!”一声不吭就走了?这留了个纸是啥?哦淦还知道把给他准备的粥和饮料拿走哦!即便气急败坏地朝外探头比亚尔也没法从日渐西斜的森森林荫下再看见那个阴沉的男人,明明救了他的命——虽然没救全还没把他败血症解决——不说谢谢了,连名字都无从得知。
比亚尔不死心的朝外又走了几步,确定没法在找到那个人后愤愤转身,捡起留在睡袋里的那张纸,想对这人唯一留下的东西发泄一番,却在看见上面血红的【寻人启事】后迅速冷却下来,联系方式上写着“祭”,也许这就是男人的名字吧...但,毕竟没人能责备一个丢了至亲而着急的人,“...哎,找人着急,找不到人自己人没了不是更没意义!”
虽然总有人说做餐饮利润很大,但比亚尔觉得以自己的的经商头脑,这相较于生意来说更像是布施,不过至少最低限度的需求有达到,甚至结缘了一个新的小小伙伴,今天的再次开业也只是回馈这些早早提着硬币来排队的回头客们——一群井井有序排队的索财灵罢了。
“所以....你就这么‘赚’够了索财灵的硬币?”听完店老板的经商理由后依旧不太相信‘营业额’的同级生维持着有些不敢置信的表情,“还多了一整箱?”“soyayo。”比亚尔将一串新鲜的韭菜穿串,摆在旁边的铁盘里,“那么这位同学,我该以干扰我正常营业为由找你讹点赔偿吗?”“...我要是说不该呢?”“那你就坐下付钱吃顿饭好了,”比亚尔把一只串着钢臂炮虾钳肉的铁签晃了晃,遥遥指着周围躲在不同地方探头观望的小小顾客们,“继续这么站着的话,我的小顾客们可不敢往前走。”
“虽然在学校里有见过...不过还未请教姓名。”一边说着,比亚尔帮唯一的大朋友摆好桌椅和简易的菜单,“客气...我是夏之理。”虽然手上接过来菜单,但夏之理更感兴趣的还是旁边一个个交上硬币后点餐翘脚等待的索财灵们,一只奥利瓦站在一字排开自清到红的锅前一个个捞起放下,后面灼灼燃烧的烧烤架上掌勺的甚至是一只赫月熊,为顾客们端来饭菜的则是一只赛富豪。“那只赛富豪是你从它们中间雇的吗?感觉不是自然进化呢。”在夏之理看来,除了服务业应有的礼貌之外,这只赛富豪肉眼可见的稚气未脱,对那些硬币甚至也会像一个索财灵一样依依不舍地放下,“确实年轻,昨天刚刚收服,当场就进化了,”预计着不会再需要额外的串,比亚尔又架起一只单独的小锅,拿起顺手的汤勺,“它起先超级不习惯的,可能也确实没人能和我一样在收服一只索财灵之前就凑齐一千枚思念吧。”再看这位意外客人,夏之理的脸色肉眼可见地爬上了浓浓的嫉妒,并用表情和抿起的嘴清晰表达自己的不满,差点让比亚尔忍不住笑出来,“别看了,就算给你喝麻辣烫的汤底也得知道你吃不吃辣不是?”“...最辣的,烧烤也是,谢谢。”
呆呆兽的尾巴是很抢手的商品,因为其本身就含有足以相称其口感与鲜美的调味物质,肥瘦相间地片下一片来以炭火烤熟就已脍炙人口,嗜辣者若是撒上以油煸香的狠辣椒辣子,刺激味蕾的疼痛就为这份鲜美增加了一份大汗淋漓的刺激,牛肉串也是烧烤的一员大将,但比亚尔更喜欢将肯泰罗的肉作为麻辣烫炖煮,与普通的牛略有差别的肉质让赤红色的滚水无法彻底将肌肉纤维硬化,纤维的缝隙渗入的水润将口感固定在丰富汁水而富有嚼劲的口感,不过铺上的淡淡辣味底色不能让老饕满意,所以比亚尔又备了一份辣树果佐制的酱料予以辅佐,本身除了尊为王的辣味外几乎没有其余的用处,却成了无法彻底渗透火热本色的肉类最好的辅佐,让灼痛和鲜嫩一并可以自口中翻滚。幸福蛋本身并不适合与辣搭配,可足够小的体积就成了外来者方便侵入的最佳理由,相较于肉,它们更多的沾染了汤底的赤红,甚至蛋黄也变成了火焰外焰一般的橘红色,作为搭配的苏糯很是协调。面包狗中有一些的身上不会出现类似于糖霜的结块,它们的面包皮毛作为原料磨制甚至可以制作面筋,这对比亚尔来说都是一个尝试,而其本身韧于寻常的口感成了它的胜原,辅佐的酱料也更容易细密渗入,让每一口都有滋有味。飘香豚作为食材的存在几乎是完美的,一份肉碎攒出的肉丸夹在烤架上便吱吱响着肉汁,下了锅中就滚滚翻着油光,独特的香味就是大汗淋漓的辣也无法彻底遮掩。烧烤架上,与油水火热碰撞过的豆腐脆生但有些干燥,配合灼人的辣像是要把嘴里的水分吸干,而另一侧吸饱了红油与汤汁的豆腐泡则像是要把整张嘴都浸润,可滚热的汤汁对辣味浸透的嘴是又一次强烈的摧残——又或者是滋润?可能对眼前的嗜辣之人而言后者更甚。用以承接麻辣烫的碗已经积蓄了许多的汤汁,已经被温热的胃袋和唇齿的灼热泼了一身汗水的夏之理挑出其中最后一块肉粒,仰头端起,甘霖般饮下,热度不减的汤汁吸饱了众多不同的味道,在名为辣的统领和热的协调下顺着舌头一路高歌猛进,彻底充满胸腹,化作一声长长的吐息随着满足一并吐出。
明明是吃一顿饭,却像是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一般,夏之理稍稍挪了挪身子,把有些饱胀的腹部闪出一些空间来。比亚尔也满足的收走这份只剩空空的碗,像是想到了什么,拍了拍身边装满硬币的箱子,“说来,看你刚才的样子,要不要从我这里‘买’点硬币?”夏之理只是撇了一眼那明晃晃的硬币便偏开头,“不用,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收集。”然后翘起嘴角,把视线和比亚尔正正对上,“既然对上视线了,这位训练师,不如以一场战斗作为这顿饭最后的结尾如何?”赌注就用一些索财灵的硬币吧,他这么说着,清晰的战意流淌出来。比亚尔擦碗的动作顿了顿,随后将它放下,伸手招呼两下,赛富豪放下工作小跑过来,而奥利瓦叹了口气接起,“...也好,我也锻炼下小朋友。不过打完之后,你还有一碗沙拉和这顿饭前得给。”